闫凯境的饮酒执念与国台酒业IPO四年困局,资本狂欢下的冷思考 闫凯境热衷“饮酒”国台IPO四年未果
- 金融分析
- 2025-04-03 04:34:09
- 8
一杯未尽的资本之酒
2023年,中国白酒行业依然在资本市场的聚光灯下炙手可热,贵州茅台以万亿市值稳坐“股王”之位,汾酒、泸州老窖等品牌亦在资本市场高歌猛进,在这片繁荣景象中,国台酒业的IPO之路却显得格外崎岖,自2019年启动上市计划以来,这家被天士力集团寄予厚望的酱酒企业,已在资本市场门口徘徊了整整四年,而背后掌舵者闫凯境的“饮酒”执念,既是国台崛起的核心动力,却也成为其资本化进程中的一道隐忧。
闫凯境的“白酒情结”:从药企少帅到酱酒狂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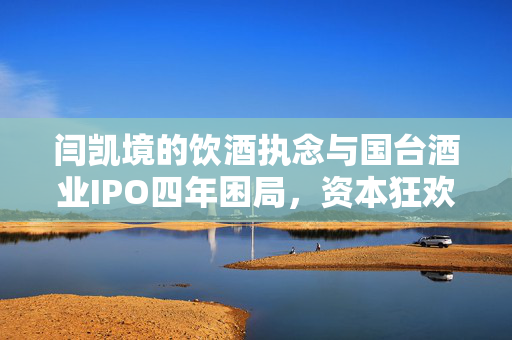
闫凯境的名字,最初与医药行业紧密相连,作为天士力集团创始人闫希军之子,他早年以“少帅”身份接棒天士力控股集团,主导了多项医药领域的资本运作,这位“药二代”的职业生涯却在2012年发生重大转折——他选择跨界白酒行业,将天士力在贵州收购的国台酒业推至台前。
这一决策背后,是闫凯境对白酒行业近乎狂热的判断,他曾公开表示:“白酒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其消费升级的空间远超医药。”为此,天士力集团向国台酒业累计注资超40亿元,从产能扩张到品牌营销,闫凯境亲自操盘每一个环节,到2020年,国台酒业营收突破40亿元,跻身酱酒第二梯队,闫凯境也被业界称为“最懂白酒的药企掌门人”。
这种“跨界豪赌”的代价也逐渐显现,天士力集团2021年财报显示,其资产负债率因白酒业务扩张攀升至57.3%,而国台酒业在提交招股书时披露的存货规模高达17.4亿元,占总资产比例超过30%,闫凯境的“饮酒”执念,正在让企业背上沉重的资本枷锁。
IPO四年未果:国台酒业的三大“绊脚石”
产能扩张与市场风险的失衡
国台酒业的招股书显示,其计划将IPO募资的70%(约25亿元)用于年产6500吨酱香型白酒技改项目,这一激进扩产计划恰逢行业调整期,中国酒业协会数据显示,2022年酱酒产能已突破70万千升,但渠道库存却高达3000亿元,市场供需矛盾尖锐,监管部门对国台的产能消化能力提出质疑,直指其“重资产投入是否具备可持续性”。
关联交易与治理结构之困
作为天士力系企业,国台酒业与集团旗下医药流通企业的关联交易始终是监管关注焦点,招股书披露,2020年国台通过关联方实现的销售额占比达12.3%,且存在向关联方拆借资金、租赁资产等复杂操作,上交所曾连续三次发出问询函,要求说明“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和“独立性缺陷”,这些问题暴露出闫凯境“家族式管理”与现代企业治理要求之间的冲突。
价格倒挂与渠道信任危机
为冲刺IPO,国台酒业在2021年将核心产品国台国标酒出厂价上调15%,导致终端价格倒挂严重,据酒类垂直平台“酒业家”调查,国台部分产品渠道库存周转周期长达18个月,经销商利润空间被压缩至5%以下,2022年,河南、山东等地经销商集体抗议,要求国台“停止压货、恢复市场秩序”,这种寅吃卯粮的激进策略,最终反噬了资本市场的信心。
资本盛宴背后的行业冷思考
国台酒业的IPO困局,折射出中国白酒行业资本化进程中的深层矛盾,资本涌入加速了行业集中度提升,头部企业凭借品牌和资金优势构筑护城河;过度金融化正在扭曲产业逻辑——酒企为迎合资本故事盲目扩产,经销商为套利囤积居奇,消费者为“面子消费”支付溢价,整个产业链的泡沫风险不断累积。
监管层的态度变化也值得玩味,2023年3月,证监会明确提出“严把上市准入关,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白酒企业IPO审核进一步趋严,这背后是对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警惕:当酒企将更多精力放在资本运作而非品质提升上,中国白酒的千年文化底蕴恐将沦为财务报表上的数字游戏。
破局之路:从“饮资本之酒”到“酿时间之味”
对于闫凯境和国台酒业而言,打破IPO僵局的关键或许在于回归行业本质,贵州酣客君台酒业创始人王为的建议颇具启示:“酱酒的价值在于时间沉淀,资本可以加速厂房建设,但无法缩短陶坛陈酿的周期。”当前,已有部分酒企开始调整策略:习酒主动终止IPO,聚焦终端动销;郎酒放缓扩产计划,投资10亿元建设科研中心,这些动作传递出一个信号——白酒行业的竞争终将回归品质、品牌与消费者体验的“铁三角”。
对国台而言,可能需要一场深刻的战略重构:降低对资本杠杆的依赖,通过数字化改造提升渠道效率;减少关联交易,引入战略投资者优化治理结构;更重要的是,克制规模冲动,将“真实年份酒”的承诺转化为可追溯的质量体系,毕竟,资本市场或许会为“故事”短暂买单,但消费者只会为“真实”长久驻足。
醉翁之意,不在酒乎?
闫凯境的“饮酒”故事,本质上是中国经济转型期的一个缩影——传统产业与资本浪潮的碰撞、企业家情怀与商业理性的博弈、短期利益与长期价值的抉择,国台酒业的IPO困局提醒我们:当一杯酒被赋予太多金融属性,它的醇香终将被资本泡沫稀释,或许,中国白酒行业需要的不是又一个上市公司,而是一份敬畏时间的匠心,毕竟,最好的资本故事,永远写在消费者的舌尖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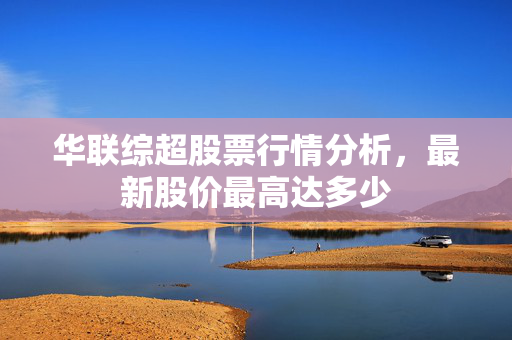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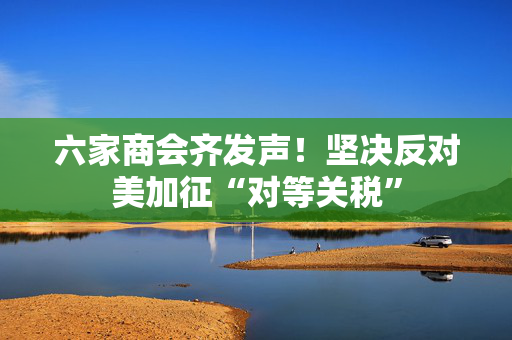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