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明天》的元叙事:告别“很久很久以前”,书写新的故事
- 金融分析
- 2025-04-16 15:27:03
- 5
我的博士导师给本科生讲电影类型时,特别喜欢打一个比方。他说:什么是电影类型呢?电影类型就是卖肥皂。如果你喜欢一种肥皂,那么你用完了这一块,还会买另一块一模一样的肥皂。但是看完一部你喜欢的电影,你不可能一直反反复复地看同一部电影,那么,类型电影,就是将一部形式、内容等多少相仿的电影,推荐给喜欢某部电影的人。它保证了相似的叙事模式和情感模式,却也提供了不同的故事,从而使得观众可以从中获得满足。
所以说,当我们看到一部电影的时候,会从电影的外部开始,先通过电影的标题、海报、预告片,再进入电影正片,从电影开场,慢慢地沿路寻找和捡起从前看电影时熟悉的碎片,通过这些碎片,我们便可以渐渐拼凑起电影大致的轮廓和走向,

《还有明天》剧照
《还有明天》不是这样一部电影。当它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黑白色调和底层视角展开城市风情画一样的开头,当镜头转向二战刚刚结束时一户普通意大利城市底层居民,以极其情节剧的方式展开他们的一天时,观众也许会期待一个致敬新现实主义的故事。然而,除了同样笑中含泪、羼杂着许多冷幽默的叙事方式之外,这部电影对前人的致敬却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重复的同时往旁边跨了一步。
这是一部通过戏仿和观众的预期玩游戏的电影。也可以说,读者越熟悉电影史,看过的电影越多,越能在这部电影中看到很多熟悉的影子,在电影打破预期时的反应也越明显。“戏仿”是一种古老的创作方式。parody的词源古希腊语中parodia的词根“para”有接近和对立两种意义。也就是说,这是一种通过模仿中的区别,通过整体相似中的不相像来表达意义。通过戏仿,一些作品可以实现自反,即在文本内部实现对自我本身的媒介、形式和表达的自我认知和呈现,在这个意义上,这样的作品就获得了一种元叙事性。
《还有明天》的有趣之处,简单说来正在于它的元叙事性。也就是说,整部电影非常自如地在很多严肃的现实主义电影叙事中穿梭,却并没有按照这些叙事套路行进。每一次我们眼见着故事情节不可避免地向一个俗套叙事的终点狂奔而去的时候,故事总是毫不费力地轻巧绕过了那个历史终结一样的终点,走向一条意料之外却情理之中的岔路。同时,电影不遗余力地通过风格化和夸张化的表达揭露这些叙事套路的人工性和虚假性;当狄更斯式的情节剧式叙事被推至极致,便会成为一种刻奇,而电影就是在这些极难掌握平衡的微妙中,用不同寻常的方式打动了观众。
全片的开场就是一个毫无预兆且动作浮夸的耳光:我们并不知道迪莉亚为何被打,但她被打了,却没有停留在这个动作上,而是若无其事地叫醒孩子,照顾瘫痪在床的公公,开始了她一天的忙碌:到富人家打针、给成衣铺做零星缝补、在修伞铺工作修伞、给全家人买菜、给全家人做饭、被丈夫打骂、和女儿一起上交工钱供丈夫饮酒狎妓,与此同时,从每天的报酬中藏起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慢慢攒起来。从她有条不紊的日常中,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且能干的劳动女性,她游走在父权制度的夹缝中,清醒且顺从地过日子,为了保护孩子毫不迟疑地去挨丈夫的毒打,但为了一成不变的灰暗生活中可能的出口和光亮,她也可以在夹缝中勉力支撑出一点自己的空间。

《还有明天》剧照
我们看到迪莉亚买菜回家的路上,跟她的旧情人尼诺见面。人到中年的修车工人,看起来很温和,但同样不富裕,生意不好,正在盘算着到北方去碰碰运气。电影没有直接呈现他们年轻时的故事,但男方显然在不断鼓励迪莉亚逃离她的丈夫。整部电影中最夸张用力地表达男女间情感的片段就是这里:迪莉亚拿出美国大兵送她的巧克力,分给尼诺,震耳欲聋的背景音乐中,慢镜头在两人中间缓慢旋转,两个人像热恋中的青年男女跳舞一般旋转着;然而背景音乐彻底压过的汽修店顾客气急败坏地在背景中喊叫,尼诺吃了巧克力后在门牙上留下的黑色污渍,让观众不断地跳出这个似乎浪漫的场景,造成相当喜剧的效果。类似这样的场景不断地质疑了情节剧中异性恋爱情的程式化表达,进而也邀请我们质疑异性恋爱情神话在女性生活中的真正意义。所以,这个表现得很夸张的陈年恋爱,在电影的结构中被构造成迪莉亚逃离的出口,却也很清晰地呈现出它的不可靠。

《还有明天》剧照
与此相对的是异性恋爱情神话明确破碎的时刻:电影里的长段家暴场景都是用极为风格化的场景呈现出来的。在用歌舞和哑剧形式呈现的暴力场景出现之前,我第一反应是想伸手捂住眼睛,但我却没有看到预期中的暴力血腥:风格化呈现的暴力变得能看下去了,它不再是直接针对感官的殴打镜头,而是伪装成社交舞蹈的互动。这些社交舞蹈本来表现的是男女之间的激情,此刻却全部转为了暴力。暴力的后果没有完全出现在镜头中,那些鲜血和伤痕只出现了一秒便消失不见,却给人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当伤痕不可见时,引发的是更深的创伤和恐惧——正常的婚姻关系和勉力装作正常的人,表面下却隐藏着一层层的伤。这种风格化的呈现反用了情节剧中情感表达的程式,却以隐喻的力量更深地指向了亲密关系中暴力的实质。
另一个反用程式的例子,出现在迪莉亚的公公死去的那个上午。令人生厌的公公在睡梦中死去,迪莉亚想到自己当天的计划,决定按下这个消息,继续若无其事地将日常进行下去。然而平日里糊里糊涂的邻居却难得英明神勇了一回,在发现老头死后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到了教堂,截住了从教堂出来的迪莉亚一家,也打断了迪莉亚骗过丈夫自由行动的计划。而平时对老父亲不闻不问百般嫌弃的丈夫立刻面对教堂下跪开始表演孝子的悲痛之情。这段场景是用非常工整的最后一秒营救式交叉剪辑表达出来的。这个在电影史上最早由格里菲斯奠定的基础剪辑方式,通过反复来回在不同地点人物的故事线之间交叉剪辑,建立了两个故事线之间的逻辑联系,而通过不断加快的剪辑频率,增加了故事的紧张感。格里菲斯用交叉剪辑讲述的故事,是无辜女子被坏人威胁,拼命赶来的男主在最后一秒英雄救美;《还有明天》中的最后一秒则是通过婚姻关系在最后一秒把无辜女子关了回去。

《还有明天》剧照
这部电影里另一处令我深思的情节是那个很明显作为工具人出现的美国黑人大兵。意大利作为二战后的战败国,盟军占领且作为暂时的治安人员维持秩序是非常常见的场景,我们也理所当然地知道,这些美国大兵在战败国具有相当高的权力。然而当我们同时清晰地知道美国此时仍然甚嚣尘上的种族隔离,了解美国黑人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会被认为不够资格上前线的时候,此时身为单纯的拯救者的美国黑人大兵,似乎也被剥离了一些可信性。他的故事是什么?除了那张黑白的全家福照片之外,我们并不知道他的来处。他非同寻常地热心和多管闲事,他细心地发现了迪莉亚身上被打的痕迹,愿意为了迪莉亚的好意而做出非常出格的报答举动,包括炸了她女儿未婚夫家的咖啡店。他的正义感,他对女性的天然同情,他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更像是一种对异文化他者的刻板印象集结,而非真实存在。想到美国黑人士兵在一战期间曾经在法国兴奋地写信回家,告诉家人巴黎人是“色盲”,完全不会因为他们是黑人而对他们另眼相看。果然所有的文化都有个理想的外部他者,而这个不在当地文化纠缠中的他者常常是走出困境的一条捷径——这个捷径却并不是彻底的解决之道。
即使是从电影情节的字面层面来理解,迪莉亚面临的困境也是一个在常规的系统之内无法解决的问题。无论是私奔逃走,还是女儿似乎高攀的婚姻,在最终都暗藏着一个定时炸弹:只要这种社会结构不改变,女性仍然只能通过婚姻逃离父权,她就没有真正可靠的出路。解开一切症结只能依靠撼动和改变这个系统。当迪莉亚在女儿和恋人的互动中回忆起自己从热恋、结婚、生育到陷入如今这般不堪的境地时,也明晰且毫不留情地告诉我们:在她年轻的时候,她同样是怀抱着希望和自己深爱的男人跨入了婚姻,当婚后丈夫显露出亲密关系中的暴力本性时,她已经无法回头。这不是选择正确的男人结婚就可以解决的,因为这个系统的问题在于,它无所不在,没有退出的可能性,而女人在其中的命运是无法靠个人的力量改变的。
所以,当电影情节走向结局,当迪莉亚躲过丈夫的审问,打开家门,穿着新衣服,以脱离樊笼奔向自由的轻盈脚步在人行道上奔跑时,我们仍然不知道她奔向的未来是否仍然处在这个结构的内部。电影前面通过女主角收拾自己的包裹和初恋情人收拾行李的镜头交叉剪辑,反复暗示我们两者之间存在逻辑联系,我们也会自然而然地想象这两条叙事线索将交汇到一起。然而并没有。当丈夫捡起迪莉亚掉落在地的重要文件,冲出家门的时候,镜头内的叙事结构还仍然似乎在走向那个逃离苦海的苦命鸳鸯的结局——直到我们看到迪莉亚和一大群女人一同走向的那个投票站。

《还有明天》剧照
这里也出现了同样的情节剧式典型的摄影和叙事方式:情节剧的基本叙事模式是“过剩”,过剩的信息,过剩的感情。在很多情节剧中,我们都会看到焦急地在人群中寻找彼此的情侣或者亲人,我们作为观众,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人都在人群中寻找着彼此,只有咫尺之遥,但他们毫无知觉,在拥挤的人群中擦肩而过。故事中没有一个人物拥有如此全知全能的视角,知晓一切的只有观众,而观众从这种过剩的信息量中为剧中人物惋惜流泪。在《还有明天》中,我们也看到了人群之中咫尺之遥却没有看见彼此的迪莉亚夫妻俩,但他们所处的场景则与催泪的叙事模式完全颠倒:我们作为观众仍然是唯一的全知全能者,而这种冗余信息只让我们为女主人公感到紧张和庆幸,和前面的最后一秒反拯救一样,异性恋的婚恋关系是不可信的结构性存在,男性不是柔弱女性的拯救者,而是捕猎者,她的拯救者在这里并不存在,她依靠的是自己。
女儿将选民证交给母亲,两人在挤满女性选民的选举地点对望,眼中充满了对彼此的支持和鼓励。而突然出现的丈夫,威胁地进入这个充满女性的空间时,站在台阶上所有女性的集体回应,是伴随着背景音乐的歌词,做了一番相当整齐的哑剧表演:
“我只有嘴里的这条舌头,即使你把这个也割掉,我也不会停下来。即使我闭着嘴,我也可以歌唱。”
她们对着慌了手脚的男人整齐地闭着嘴哼唱着,此时,第四面墙终于完全打破——这是对父权的宣言,也是对电影院中观众的自我表达。
“我们紧握选票,就像紧握情书。”(安娜·加洛法罗)正如电影中虚构的故事结束,历史上的新闻纪录片片段出现时,银幕上的信息告诉我们的那样,这是一句历史上的女性运动者确实说过的话。在这个意义上,整部电影就是生长在这句奇妙譬喻上的一个包袱,包含的信息非常简洁明了,甚至有点硬:比起情书,我们更需要的是选票。
但是这个信息外面包裹的包袱却不是一个纯然现实主义的故事:这个在影像风格和故事场景上都多少接近新现实主义的叙事,本身无意让人将这段影像与真实故事混淆:这个故事里太多缺口,太多暗示,太多不合理,不断提醒我们不要全然相信这个过于夸张的、近乎漫画式的情节。而在这样过剩的信息海洋中,我们作为观众,应该相信什么?

《还有明天》剧照
当故事中充满了情节剧式的滥俗套路式,却也有那么多格外鲜活的深入生活肌理的细节,就像修伞铺笨手笨脚的男学徒,打针时克扣工钱的富人家,藏在缝纫机抽屉碎布后面的重要文件,好朋友之间悄悄躲起来分享的一支烟,藏在内衣里的私房钱,藏在外衣下面的家暴伤痕……是这些女性生活中自然流露,真实可信的细节支撑起了整部电影的情感力量。这些细节不会出现在一个以男性为主人公的叙事中,因为它们与一个女人在父权制压迫下的经验血肉相连。同样是这些可信的细节,质疑了那些和“很久很久以前”相伴相生的套路和情感表达,而更多呈现出女性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生存境遇,她的抉择和她的反抗。
情节剧其实往往是很难维持真实感的。过时几十年的家庭伦理剧中的意识形态和情感表达方式往往会让现代人大皱眉头。《还有明天》也用自己的方式隐喻性地表达了这个信息:我们熟悉过去的故事写作方式,而在明天,我们应当换一种写作方式。
当然,我们也知道,1946年意大利的全民公投,决定的是战后国家的政体:更多的人选择了共和制,而非君主制。这不是一个与女性个体权利直接相关的议题。然而,只要可以发出声音,永远会有明天。
下一篇:新机遇涌现,宏达新材股票连续涨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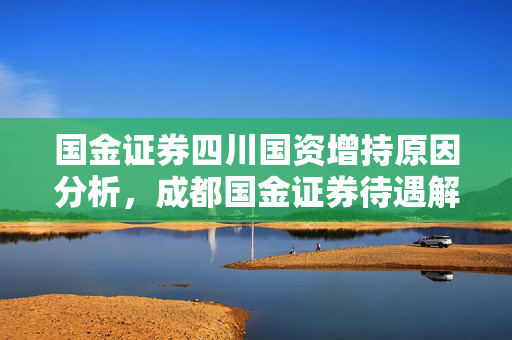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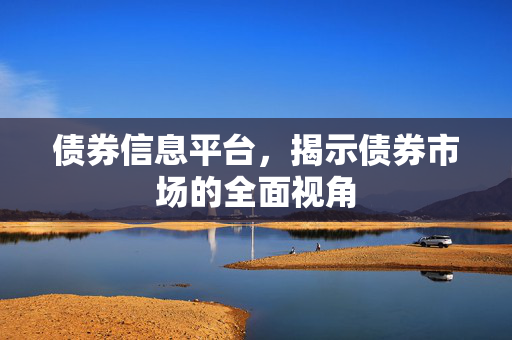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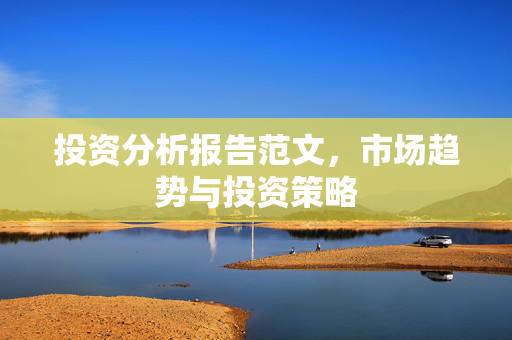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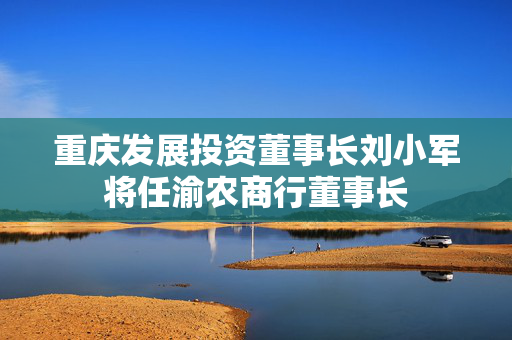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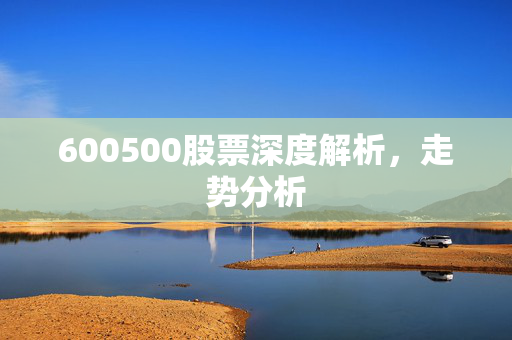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