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擒故纵:公司并购交易中的招揽权
- 金融分析
- 2025-03-19 16:59:52
- 27
从前介绍并购交易中的分手费的时候,清澄君曾经提到分手费条款与并购协议中的另一项安排有很大关系,那就是招揽权(go-shop)。什么是招揽权?它因何而起,有哪些特征,又会带给并购交易什么样的影响呢?且听清澄君解说其详。
背景
1986年特拉华最高法院在Revlon, Inc. v. MacAndrews & Forbes Holdings, Inc.一案的判决中确立的著名的“露华浓规则”(Revlon rule),要求目标公司董事会在出售公司控制权时为股东们寻找可能的最佳收购方案。为满足这一要求,目标公司董事会几乎不可避免要在确定最终买家之前进行寻价。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寻价的主要方式是由目标公司董事会通过投行搜寻潜在买家,随后组织一场正式或半正式的拍卖式竞价,包括与切实有兴趣的买家签订保密协议,要求其作出初步报价,再从中挑选部分买家进行深入的尽职调查,邀请其参与最终竞价。完成这一竞价程序后,目标公司董事会将确定属意的买家签订并购协议并正式向市场公告。
在此类并购协议中,为增强交易的确定性,卖方通常会承诺不再主动招揽其他买家,也就是约定所谓的“禁止招揽”(no-shop)条款。不过,出于董事会的忠慎义务(fiduciary duty),卖方仍会保留考虑不请自来的收购建议的权利,如果认定该建议比并购协议的条件更为优越,也就是构成所谓的“更优方案”(superior proposal),那么,卖方可以与提出此建议的第三方进行磋商,乃至转而与之签订并购协议。这一安排被称为“基于忠慎义务之例外”(fiduciary out)。
2003年在特拉华最高法院作出Omnicare, Inc. v. NCS Healthcare, Inc.判决之后,“基于忠慎义务之例外”成为卖方董事会满足自身义务的标配。于是,禁止招揽加基于忠慎义务之例外就成了“露华浓规则”之下的一种典型并购交易方式(在安邦与万豪竞购喜达屋的过程中,我们就见到过这种方式)。
不过,以上这种典型的寻价方式虽然适合战略投资人收购,却会给财务投资人的收购造成困扰,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并购对前者多具有协同效应(synergy),而对后者却常常没有这样的效应。由于各家战略投资人自身条件不同,其能享受到的协同效应也不一样,因此,对各家而言,目标公司的价值也就产生了差异。在拍卖式的竞价机制下,认为目标公司对自身的价值最高的战略投资人也最有可能报出最高的价格,从而最终购得目标公司。
可是,对于没有协同效应的各家财务投资人而言,目标公司无论对谁价值几乎都一样。多家财务投资人参与目标公司的拍卖竞价,最后获胜的那一家必定因为其出价比别家都高。然而,既然目标公司对各家的实际价值相同,那么出价最高者显然也比其他人高估了这个实际价值。
假如各家财务投资人掌握的信息相似,那么,从概率上说,作出最高估价的那家也最有可能估值错误(英谚有云:两人智慧胜一人(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因此,赢得拍卖的这家其实最有可能是倒霉蛋。这就是所谓的同值拍卖(common-value auction)中出现的“胜者之诅咒”(winner’s curse)(Denton, Stacked Deck: Go-Shops and Auction Theory,Stanford Law Review2008)。
21世纪初期,为应对dot-com泡沫崩溃后的经济衰退,美联储大幅削减利率,信贷随之活跃,市场上的资金大大充沛起来,其中大量资金流向私募基金。从2003年中期开始,美国经济呈现复苏,并购市场也进入了史上第六轮的高潮期。银根宽松加上Sarbanes Oxley法收紧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使得由私募基金发起的杠杆收购私有化交易成为此轮高潮的一个显著特点。
然而,大量的私募基金竞争相对较少的投资机会将令这些财务投资人在拍卖竞价过程中陷入更为严重“胜者之诅咒”之中(3家竞价,胜出的一家还有可能真的才智高明估对了价;300家竞价的话,打败299家的那位就几乎注定是冤大头了)。为此,财务投资人们急切盼望改变原来的寻价方式,谋求在目标公司还没有组织拍卖竞价之前先取得排他性接触磋商的机会。
可是这样一来,再要坚持签约之后禁止招揽,就可能无法达到“露华浓规则”的要求。于是,财务投资人们想出一种变通方法,待他们与卖家正式签订并购协议并向市场公布之后,再给予卖家一段时间招揽第三方出价。这就是事前不竞价,事后再寻价的“招揽权”条款的核心内容。
特拉华法院在确立“露华浓规则”之后不久就表示事前竞价并非满足该规则的唯一途径(Barkan v. Amsted Indus., Inc.),其实,早在1988年特拉华衡平法院就曾认可事后寻价(In re Fort Howard Corp. Shareholders Litigation)。当时,实务界认为在并购协议中规定目标公司有权于签约后考虑不请自来的收购建议,并在宣布交易的公告中说明这种权利,再辅之以较低的分手费(交易金额的1.9%到2.2%)和较长的宣布-交割窗口期,即可构成签约之后的“隐性市场排查”(implicit market check)。这可谓招揽权的雏形,2007年,特拉华衡平法院在In re Topps Company Shareholders Litigation的判决中首次明确承认招揽权条款可以用来满足目标公司董事会在“露华浓规则”下的忠慎义务。
趋势
清澄君从MergerMetrics数据库搜集了自2003年至2016年11月8日宣布并已完成的所有收购100%美国公司股权的友善并购交易共2977件,图1展示了这14年间出现招揽权条款的交易占各年交易总数的比例。
该图显示2003年尚无含招揽权条款的交易,2004和2005年此类交易初现端倪,到2006年则出现了第一次大增长。这一增长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2006年私募基金完成的并购交易大幅增长,交易金额从2005年的1760亿美元增加到4146亿美元,涨幅近1.5倍;而其占全部并购交易金额的比例也从2005年的19%猛增到32%(Thomson Reuters, Mergers & Acquisitions Review 2006 Q4)。
图1 2003-2016含招揽权条款交易占比
2007年随着特拉华法院态度的明朗,招揽权的运用日益频繁,图1清晰展现了这一态势。尽管在金融危机期间,招揽权的运用比例略有下降,但降幅并不大,而到危机之后的2010年其使用比例再次大增。不过,这一次的招揽权热可能是因为从金融危机开始,战略投资人也日益青睐招揽权机制,图2大体展现了这种趋势。
图2 2003-2016战略投资人使用招揽权比例(%)
结构
招揽期限
招揽权条款的基本结构是允许卖方在签约后的一段时间内主动招揽其他买家竞价,如果出现更加优越的竞购条件,卖方就可以与之磋商乃至终止原先的并购协议,转而出售给这样的新买家。卖方招揽的期限通常为20-55天,平均为35天左右。图3显示的是在清澄君搜集到的并购交易数据中招揽期限长度的频率分布,其中可见长度为30-35天的招揽期限出现频率最高,最短5天,最长85天,平均为34.5天。
图3 2003-2016招揽期限频率分布
还值得一提的是,招揽期限通常指的只是经招揽出现更优方案的时限,而非与提出这种方案的第三方完成磋商、签订并购协议的时限。只要在招揽期限内提出更优方案,该第三方就可以享有合理的时间与卖方进行磋商和签约,哪怕延续到招揽期限之后。这样的第三方因为无需支付以下介绍的分层分手费中较高的那一层分手费,所以常被称作“除外方”(Excluded Party)。对于未约定此类“除外方”的招揽权,特拉华法院曾提出质疑(In re Lear Corp. Shareholders Litigation)。
分层分手费
与招揽期限紧密相关的是分层分手费设计,既然允许卖方招揽,那么,因为在招揽期限内出现更优收购方案而终止原先协议的,分手费就不能太高;而在招揽期过后,卖方不能继续主动招揽,此时出现更优方案最终导致卖方(由于董事会负有的忠慎义务)终止原协议,转投新买家的,分手费便要增加。就这样,分手费分出了层次,前一层分手费的比例一般占交易金额的1%-2%,而后一层次的分手费比例则提高到3%-4%。
前面已经说过,目标公司对各家财务投资人的价值往往相差无几,这些买家之间的竞价属于同值拍卖。此时,如果将分手费提得很高,会让抢先签订并购协议的买家取得明显优势,更可能阻遏其他买家竞价。后来参与竞价的买家想要获胜,不但要报价超过前面的买家,还要负担向前面的买家支付的分手费。因此,目标公司对后来买家的价值至少要超过在先买家的出价与分手费之和,这对参与同值拍卖的财务投资人而言常常不现实。
于是,压低招揽期限的分手费金额就成为方便事后寻价的重要手段(Denton, Stacked Deck: Go-Shops and Auction Theory, Stanford Law Review2008),特拉华法院也肯定了分层分手费促进目标公司董事会履行忠慎义务的积极意义(In re Topps Company Shareholders Litigation)。不过,即便运用了分层分手费,也许由于对目标的估值过于近似,财务投资人仍很少在招揽期间积极竞价。有研究发现,在此期间参与竞价的几乎全是具有协同效应的战略投资人(Denton, Stacked Deck: Go-Shops and Auction Theory, Stanford Law Review2008)。
提价权(match right)与信息共享
在先签订并购协议的买家为保护自己最终完成交易的机会,经常会在协议中加入提价权条款。据此,如果有第三方提出更优方案,在先协议方可于一定期限内提价,以求超越第三方的更优方案。此后,第三方也可能再提出一个更优方案,而在先协议方又可以再次提价,如此可以循环往复多次(为避免过多的循环,卖方可以约定提价的次数或者最终时限)。提价权行使的期限通常为3-5天。需要指出的是,提价权并非包含招揽权的并购协议独有,约定禁止招揽的协议也可以有提价权,但招揽权的运用或许让提价权出现得更为频繁。
要确保提价有的放矢,在先签约方就不能在信息上处于劣势,所以,招揽权条款也经常包含信息分享的要求。就是说如果卖方向后来的竞价方提供了“实质性非公开信息”,那么,这些信息也必须提供给在先签约方,以便其作出提价决定。由此,信息分享确保在先签约方掌握的信息不会少于事后参与竞价的第三方。而提价权与信息分享结合无疑再次降低了第三方竞价成功的概率——面对掌握的信息不必自己少,又有权提价的在先签约方,第三方即使认定最初的并购协议价格过低也可能不愿参与竞价。
以上介绍的招揽期限的长短、分层分手费的高低、提价权以及信息分享要求的有无都是实务中有关招揽权条款谈判的重点。
特征
相比不含招揽权的并购交易,包含这种权利的交易在当事方与交易设计方面有些什么样的特征呢?以下不妨根据清澄君搜集数据一窥究竟。表1比较了这两类交易的多方面特征,其中最后一列标有星号的表示两者的差异从统计角度看几乎不可能是随机因素造成的。
表1 2003-2016有无招揽权并购交易特征比较
*表示具有5%以上的统计重要性。
先看交易双方的特征。很明显,在有招揽权的交易中,收购方是财务投资人的比例远远高于没有招揽权的交易,这与前面介绍的招揽权出现的背景相符。而在目标公司方面,有招揽权的交易更多涉及收购注册于特拉华州的公司,这或许和特拉华州存在“露华浓规则”,以及认可招揽权可以满足该规则的判例相关。
再看交易设计的特征。首先,有无招揽权看似与交易金额无关。不过,表1没有显示出来的是,如果我们只比较财务投资人作为买方的交易,那么,没有招揽权的交易平均金额(11.24亿美元)明显小于有招揽权的交易(25.71亿美元),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完全一致(Subramanian, Go-Shops vs. No-Shops in Private Equity Deals: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The Business Lawyer2008)。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又与特拉华的法律相关。
2007年特拉华衡平法院在In re Netsmart Technologies, Inc. Shareholders Litigation一案的判决中表示,与招揽权类似的事后寻价机制(Netsmart案本身虽然不涉及招揽权,但包含“隐性市场排查”这种事后寻价机制)更适合大额交易,而不适合“微市值”(micro-cap)交易。主要理由在于:后来的竞价者为了胜出所需花费的交易成本(包括聘请顾问的费用及其参与竞价和竞价失败带来市场关注的声誉成本)大致是固定的,而金额越大的交易潜在收益越大,因此,相比小额交易,大额交易更可能吸引后来竞价者。
第二,有招揽权的交易明显更多使用全现金支付方式,相应地,这类交易更少采用全股票支付。这个特征又与特拉华公司法紧密相连。在前面的“背景”部分,清澄君已经说明,招揽权是为应对特拉华州的“露华浓规则”而形成的一种寻价模式,因此,受该规则制约的交易自然更有可能加入招揽权条款。
有趣的是,根据特拉华州的判例法,“露华浓规则”是否适用与收购对价的支付形式息息相关。简言之,100%采用现金支付的交易几乎肯定适用这项规则,反过来,100%以股票支付的交易除非涉及控制权移转,否则基本不适用“露华浓规则”。
居于这两者之间的交易,目前特拉华判例法的态度是:使用现金比例超过50%的将激活此规则(In re Smurfit-Stone Container Corp. Shareholders Litigation),而现金比例不到33%的则不会激活“露华浓”(In re Santa Fe Pacific Corp. Shareholders Litigation)。对照这样的判例规则,全现金交易中更多出现招揽权就不奇怪了。
接下来,表1显示有招揽权的交易更多属于私有化交易、杠杆收购或者管理层收购交易。由于这些形式的交易与财务投资人发动的收购高度相关,而财务投资人更多使用招揽权,因此,它们更多和招揽权并现也就顺理成章。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管理层原本就掌握更多的公司信息,所以,当他们与财务投资人联合发起管理层收购,并且采用招揽权条款这种事后寻价机制的时候,更难指望有其他买家——尤其是财务投资人——参与竞价。谁要出价比管理层还高,恐怕十有八九是中了“诅咒”了,研究也发现在包含招揽权的管理层收购中确实没有事后竞价者出现(Subramanian, Go-Shops vs. No-Shops in Private Equity Deals: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The Business Lawyer2008)。
再往下我们发现有招揽权的交易也更多包含提价权,这一点与上文“结构”部分的介绍一致。不过,采用招揽权的交易中提价权的行使期限似乎更短,这多少有些出乎意料。或许体现了买卖双方在谈判招揽权条款过程中取得的某种平衡,是买方向卖方作出的一种让步。
随后,我们看到在含招揽权的交易中双方约定分手费的可能性都更高。金融学者的研究表明:卖方约定分手费增加了交易确定性,有助于提高买方的报价(Officer, Termination Fees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3)。而清澄君上面分析过,在财务投资人发动的包含招揽权安排的交易中,分手费更会产生阻遏后来竞价者的作用,换言之,此时对在先签订协议者来说交易的确定性更大,所以分手费产生的提高报价的作用应当更为明显。
对并购交易中的反向分手费的作用,通常有两种认识。其一是认为它是买方向卖方传递的信号,表示买方对满足各项监管要求、完成交易信心十足,从而增加竞价胜出的机会。这一作用在交易面临反垄断审查的情况下尤为重要,比如清澄君从前介绍过的谷歌收购摩托罗拉交易中的反向分手费。不过,这种功能在包含招揽权的交易中似乎作用不大,因为此类交易的买方多为财务投资人,反垄断问题并不十分突出。
其二是认为反向分手费有如买方购得的一种期权,在需要走开的时候,买方可以干净利落地走开,而不必担心卖家寻求实际履行(Mahmudi et al., When a Buyer Gets Cold Feet: What Is the Value of a Bidder Termination Provision in a Takeover, working paper2016)。这一功能对于实施杠杆收购,因而面临融资风险的财务投资人的确具有积极意义,一旦债务融资无法到位,买方可以支付反向分手费终止交易。
然而,从法律角度看,买方被要求实际履行的情况应当更有可能出现在以股票(或者至少是部分股票)作为收购对价的交易中,因为这样的交易卖方更有理由主张买方的违约给自己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害”(irreparable harm),特拉华法院的态度也确是如此(In re IBP, Inc. Shareholders Litigation,不过本案所涉并购协议适用的是纽约州法律),而包含招揽权的交易大多为全现金交易,面临实际履行的威胁应当不大。因此,在此类交易中约定反向分手费也许可以理解为买方的谨慎,毕竟有其他州(如田纳西州)的法院曾要求买方在全现金交易中实际履行并购协议(Genesco Inc. v. Finish Line Inc.)。
另一方面,在约定了分手费或反向分手费的交易中,这些费用占交易金额的比例并不因有无招揽权而有分别。就分手费的比例而言这似乎略显奇怪,前面我们说过,在包含招揽权的交易中分手费更不利于吸引竞价,因而至少有必要在招揽期间压低分手费。
从表1中我们没有看到含招揽权的交易分手费比例更低,也许是因为MergerMetrics的数据只报告了较高的那一层分手费。不过,此前的研究好像也没有发现招揽权对分手费金额有显著影响(Subramanian, Go-Shops vs. No-Shops in Private Equity Deals: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The Business Lawyer 2008)。
最后,我们似乎没有发现并购协议签订后出现第三方竞购的概率因为包含招揽权而下降,这与招揽权机制让在先签订协议者掌握更多先发优势的理论不符,倒是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先前相关研究发现招揽权的确能发挥吸引第三方竞价作用的结论相吻合(Subramanian, Go-Shops vs. No-Shops in Private Equity Deals: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The Business Lawyer2008)。只是表1显示的第三方竞购的比例要比早前的发现低许多(Subramanian发现含招揽权的交易中deal jumping的比例是12.5%)。
影响
招揽权机制会对并购交易进程以及目标公司股东的收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方面迄今最好的经验研究当属哈佛大学法学院Subramanian教授2008年发表的文章。
Subramanian教授搜集了2006年1月至2007年8月间宣布的美国市场上所有由私募基金参与的私有化交易总共141件。其中包含招揽权的48件,他将这48件交易又分为并购协议签订前进行过寻价的招揽权(称为“附加招揽权”)与完全没有事前寻价的招揽权(称为“纯粹招揽权”),后者占大多数(60%)。
他发现招揽权对交易进程产生的第一个影响就是让卖家的事后寻价切实变得活跃起来。在禁止招揽的交易中,买家当然不能积极寻求事后竞价,而出现不请自来的事后要约的比例大概是8%。相反,在包含附加招揽权的交易中,卖方在签约后(通过投行)平均会联系33家潜在买家,而在包含纯粹招揽权的交易中这一数字更扩大到近40家。
综合签约前后的情况,Subramanian发现包含招揽权的交易中卖家联系的潜在买家的平均数量其实超过禁止招揽的交易(含附加招揽权的交易为48.9家,含纯粹招揽权的交易为40.6家,而禁止招揽的交易只有31.6家)。这说明招揽权条款绝非摆设,而是实实在在发挥了招揽的作用。
然而,另一个让人吃惊的发现是:尽管在含招揽权的交易中卖方联系的潜在买家的数量超过禁止招揽的交易,可是,若从签订保密协议进而开始认真考虑收购的买家数量看,禁止招揽的交易就远远超过含有招揽权的交易(禁止招揽的交易平均有16.1家,含附加招揽权的交易为1.5家,含纯粹招揽权的交易为3.2家)。换句话说,招揽权虽然让卖家招了买家,却揽不住他们。
Subramanian教授最重要的发现有关招揽权对目标公司股东收益的影响。他发现虽然含附加招揽权的交易不比禁止招揽的交易带给目标公司股东更高的收益,但是,纯粹招揽权却给目标公司股东们多带来了大约5%的超常收益(abnormal return)。因此,综合起来看,特拉华法院承认招揽权机制是与事前竞价+禁止招揽+基于忠慎义务的例外这一机制相当的满足“露华浓规则”的寻价途径似乎不无道理。
那么,揽不住潜在买家的招揽权究竟缘何让目标公司的股东受益呢?一些实务界人士认为这是因为招揽权机制让卖家得以先签下一个买家,从而建立起一个托底的收购价格,而同时又可以借助招揽第三方的压力作为与签约买家的谈判的筹码。简言之,就是招揽权让卖家得以“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不过,Subramanian教授认为这种理解无法解释为何能以更低价格购得目标公司的买家会愿意出高价采用招揽权。因此,他提出招揽权提升收购价格的原因应该出在买家的动机上。具体来说,由于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收费采用的是年2%的管理费加20%的收益提成,投资能不能有收益虽然不确定,可是只要把钱投出去,2%的管理费却肯定是会来的。
所以,私募基金的动力在于不断扩大投资规模,从而挣得更多的管理费。募集到的钱如果投不出去就要退还投资人,管理费也不得进账,于是,私募基金首重交易成功的概率,而不是交易能带来多少净收益。由于具有排他谈判和在先签约权的招揽权机制让交易成功率大大提升(据Subramanian教授测算,在禁止招揽的交易中私募基金完成交易的概率只有6%,而在包含纯粹招揽权的交易中却高达86%),它自然也就成了私募基金不惜高价寻求的交易方式。
这样看来,尽管招揽权可能成为目标公司股东的福音,但对买方的投资人来说,又是一项不折不扣的代理人成本了。不过,应当指出Subramanian教授研究所据的样本比较小,运用的统计方法也比较简单,因此,以上发现还是比较初步的。另外,此前更加系统的研究发现私募基金买家比上市公司买家支付的收购价格更低(Bargeron et al., Why Do Private Acquirers Pay So Little Compared to Public Acquirer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8),这一现象看似与Subramanian的发现也不甚吻合。
“招揽权”这个词乍听起来像是卖方获得的一种权利,而有权招揽更多竞价者仿佛也会给买方带来更多的交易风险。然而,当我们了解了招揽权的来龙去脉之后就会发现:这项权利不仅是买方主动赋予卖方的,而且还可能为此支付了更高的买价;与此相应的是,运用招揽权之后,买家完成交易的确定性不仅没有减小,反而大大增加了。招揽权实在可谓是财务投资人一招欲擒故纵的妙棋。
“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实际上,招揽权与并购协议中的其他各种设计一样,都是在自由市场条件下由交易当事人自发形成的双赢机制——在此,买方得到了交易确定性,卖方则获得了更高的对价。我们眼前呈现出的似乎正是已故诺奖得主科斯老先生半个多世纪前向我们展示的那幅私人自发创造效率的美妙图景(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60)。
“等一等,”也许你要说:“这幅市场的图景并不美妙,清澄君难道忘了招揽权背后困扰着私募基金的代理人问题了吗?”的确,想到这一点着实有些叫人揪心。不过,要克服市场中的问题,最终恐怕还得靠市场的竞争。尽管目前的研究还不足以告诉我们那些信誉卓著私募基金是不是也会不顾回报,一味利用招揽权谋求扩大投资规模,不过,我们至少知道有一位投资界的泰山北斗是不屑那样做的。
写到这里,清澄君不由想起另一位诺奖得主打的一个有名的比方。斯蒂格勒(Stigler)曾说,认为市场失灵便需要政府监管,那就好比一场两个人参加的钢琴比赛,裁判刚听完第一个人的演奏,随即就将奖牌发给第二个人。所以,监管者恐怕大可不必为举牌线设在5%、4%,抑或1%而烦恼,也更不用将按市场规则出牌的玩家称作什么“害人精”。
来源:比较公司治理(ID:bijiaogongsizhili)授权转载
版权声明
我们尊重每一位原创作者的心血,转载均注明文章作者及来源。若涉及版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第一时间处理。
聚人|聚项目|聚资金| 聚智慧
微信ID:JiuYoCapital
长按左侧二维码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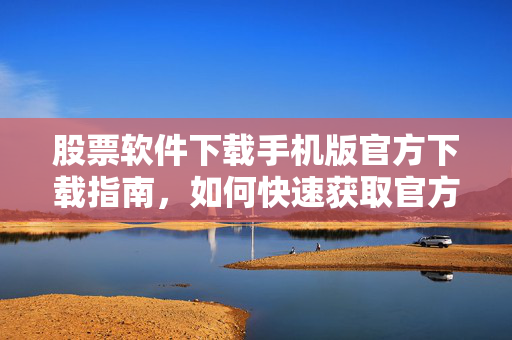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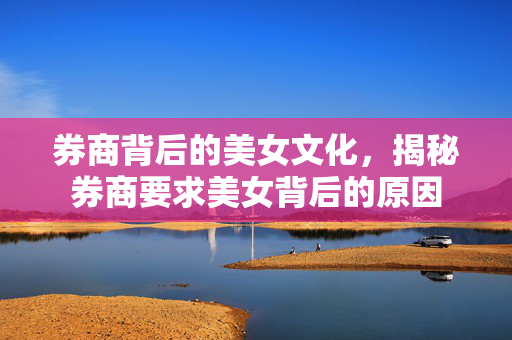










有话要说...